乌夜啼(外一篇)
夜晚,我独自坐在窗前,面前摊摆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《乌夜啼》,我并没有开灯,只是拉开窗帘,任凄美的月光洒在我的桌上,时光倒转至公元977年。
就在这个晚上,我将盛饭的篮子提到“赐第”,您知道这是我的职责。我看到篮子里面只是几碟素菜,一盆饭,与两只青花瓷碗。我将饭菜摆放好,便起身朝我的主人李煜的卧房走去。“主子,吃饭了。”我轻声喊道。过了许久,房里才传来他清寒而又沙哑的声音:“我知道了,你先去吧。”我颔首退出,在门外静候着。嘎的一声,门突然打开了,他看了看还在门边静候的我,皱了皱眉头,轻声道:“不是叫你先过去吃么?”我抬头望了望他,又低下头来,我知道他还在看着我,等待着我退出,但我却不敢面对他。“唉……”他轻叹一声,便领着我走向前厅。自从被赵匡胤软禁在“赐第”中,他的性格便转变了许多,现在他已将我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当作家人对待了,平起平坐,共叙家伦,仿佛我已不是一个侍候他的奴婢。
吃罢饭,我将篮子送到“赐第”外,不久就会有人将它拿走。我起身走回楼上,准备侍候他写字,但待我来到书房,却又不见他的身影,于是我走到“西楼”那个他常呆的地方,顺便拿了件外衣。待我上去,我便看见他一人静默地站着,晚风把他的头发吹得零乱,那青色的衣角也在频频拍打着他的身体。院里的梧桐树好像也配合这凄凉的情调,巨大的叶片飒飒落下,竟飘向二楼。李煜拾起一枚被秋风染黄的叶子,静静地看着,似乎有诗意在他心中萌动。我不忍打扰他,却又害怕他单薄的身子受不住寒风的侵袭,便走上前去将外衣轻轻披在他身上。“谢谢!”他对我轻声道。我抬眼看他苍白的脸色在月光下像两页白纸,洁净但了无生机。我眼睛潮潮的,便退到他身后。“外面风大,你还是进去吧。”我对着他抖抖的背影说道。他侧过脸来,嘴角随意地勾了勾说:“你先进去吧,我还想再待会儿,当心着凉。”我借着清冷的月光看他,他的脸上还有几条未干的泪痕。“你不进去,我便陪你在外边站着。”我倔强地说道。他听我这样说,便又把头转回,不再做声。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我的身子已冻得麻木,强忍的咳嗽也咳出来,我低下头,泪水打在青石板上,溅起一朵小水花。突然有一个东西披在我身后,我抬头向右看,原来是他把衣服披在我身上。“进去吧。”他拉起我早已冻得冰凉的手。待身体恢复知觉后,他便走到桌旁,我知道他准备写词了,我忙跑过去替他研墨。
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
“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
他挥笔写就,一滴泪落下,把未干的朱墨染开来,像一簇桃花。我看着这几行字,想问:“你,怎么……”我欲言又止。他轻轻地摇了摇头,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。“你不要再意志消沉了,我明白唐亡并不全都是你……”他抬头看了看我:“不全都怎样,不全都又能如何?”他自嘲,“我又怎会不明,是我错了,如果当初不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,唐,又怎么会亡,而现在这一切都是我自信自守,自作自受。”他沙哑的声音随着他的脚步声,随着乌鸦凄厉的啼鸣,渐行渐远,渐行,渐远……
公元978年,乌鸦不再在此啼鸣,那位高妙的词手已被宋太宗赐死于“赐第”。
我醒来,发现自己伏在《绝妙好词》上睡了不大一会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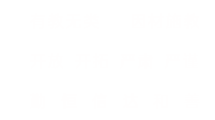
 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
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



